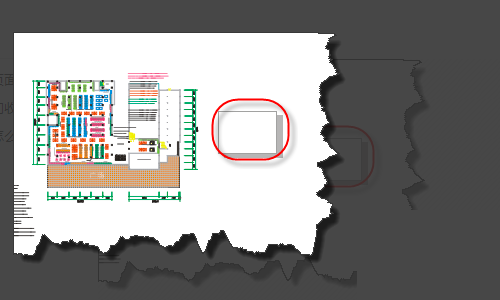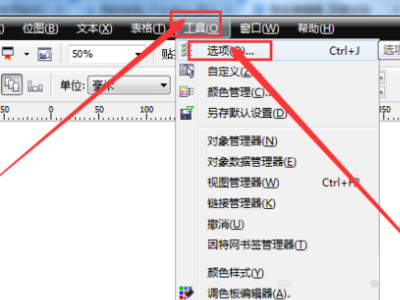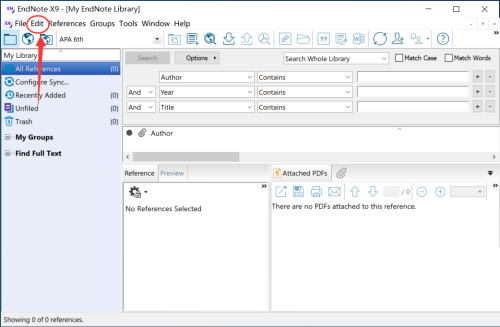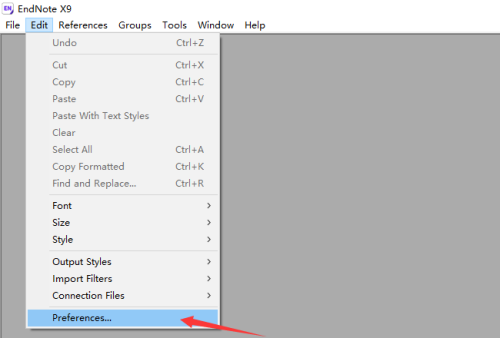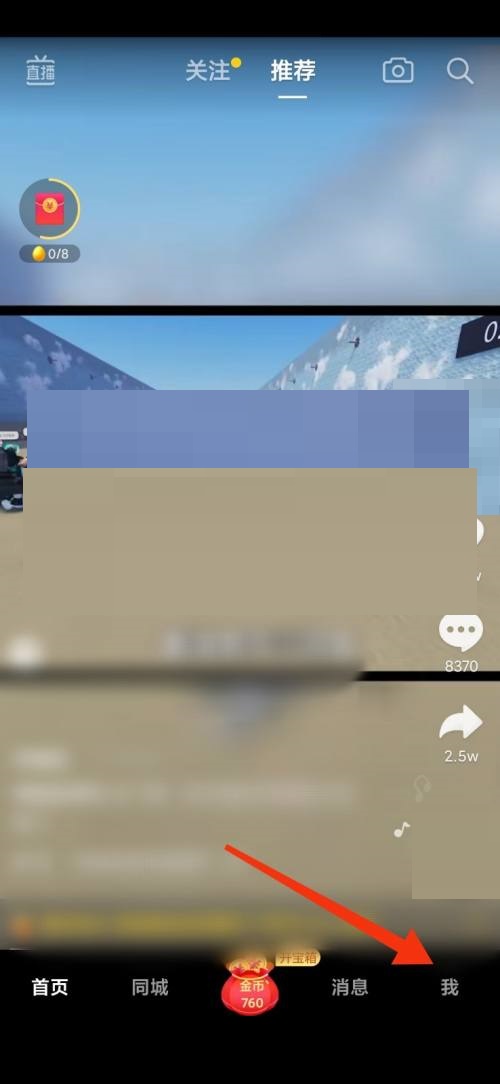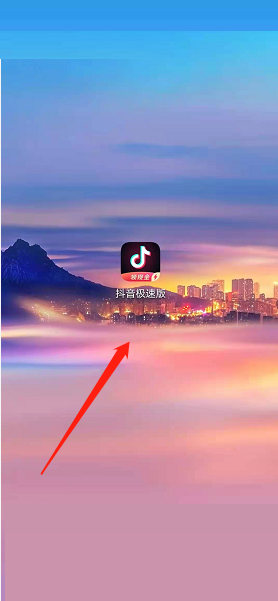午夜来电,心紧。
两个多月前的深夜,我在上海接到来自堪培拉的电话。来电者的第一重身份,是多年前,我在悉尼生活期间一位挚友的前女友,他们分手后,我们依然有交往,大家叫她安。电话里的声音是沉着的,安想要她前男友李修的联络方法,并礼貌地让我先问一下对方是否愿意。1996年后,他俩二十多年无联络,现在突然要找对方,事非寻常,我先把联络方法给了她,通报李修是次日。
堪培拉来电后一周,他俩都没和我联系,我虽好奇,但没有探问。又过几日,我得新冠第二日,正发烧、畏冷、咳嗽、浑身酸痛。伸一只手在棉被外接电话,都会冷得浑身打颤,喷嚏一来就是七八个。此时李修来电,说了安找他的事由,出乎我的意料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李修,一个很特别的人,我和他三十多年交情,达到了这样的默契,无论我怎么写他,都可以先发布再报告。去年十一月,我在一篇两千字的短文里,写过和安分手时,他的种种失控。他读后傻笑了一下,问,她看到这番描写,得意了吧?
我知道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,客观上帮李修传递了不甘,又方便他极自尊地抵赖。其实,他并不需要我代劳,因为他从不虚掩什么。
而安,曾告诉我,她现在的伴侣对她很包容。安对情感的觉悟已很通透,但还保留着多年不变的老到,从不谈李修。
那一年,我们四对好友全部分手,在悉尼。
不管法理上属哪种关系,分离却是骨断筋连的那种。内心的破碎感,大家都整理了很久。男女携手谋生域外,实为一段段苦心孤诣的缀网劳蛛。移居初期的诸般心累,不时榨压出各自秉性中本已存在的低劣部分。焦躁多了,龃龉多了,伤害多了,如胶似漆的两人,转眼就成距离最近的仇家。放过或放下,不是随意就可摆出的翩翩风度。这看上去像是男悲女哀,其实却是第一代移居者的灵肉之殇。
当时,四男之一的李修曾苦笑着预言,以后,我们可能发展成16个人,可否相约在那时欢聚一次?众男脸皮厚一些,全票通过。二十多年后,也就是2022年,李修在鄂皖山区建了一个别墅,想兑现当年胡诌的16人晚餐。信息一出,相关的女士部分举手报名,而先生们的呼应竟并不兴奋。费解。
安找李修,是因为她父亲在国内的养老院病危,急需亲人介入。安一时无法成行,国内可数的几位亲戚,多为老弱。安有表哥表姐,常年如子女般服侍安父,老人弥留之际,表哥表姐也得病需别人照料了。安拉了一个紧急求援的候选名单,最后一名赫然写着:李修。尴尬是极尴尬,但眼下已无选择。安从一名普通的中国留学生,成为澳洲国家博物馆负责亚太板块的资深专家,不简单。多年的修炼,让她有能力从一堆乱麻中,直接挑出一根压倒众绳的主线,这就有了那个午夜来电。
安和李修联络后的第三日,安父溘然离世。原本托付的事宜,叠加了内容。安把后事的料理郑重托付给李修,此刻正是他患新冠第三日,他说没事。
异地间的托付,本为常事,但这一次,李修是在冷汗涟涟中受托,在冷汗涟涟及各种酸痛和眩晕中,连续几天迎风出门,直至亲手落实最后一项,即老人的骨灰存放。安及她在悉尼的家人,对李修本人的状态十分关切,李修还是说没事。
这正是很寒冷的一段日子,不难想象高烧中的李修,连续多日奔走在湖北的寒风里,会是什么滋味。李修说,对于从风浪里过来的男人,这些不提也罢。李修说,任何朋友在这种状况下的这种托付,他都会这样对待。
是吗?当然,以李修所说为准。
我觉得,本次托付首先是安的果决,她理解生活中某些时刻会别无选择;她懂得某些时刻必须以最简明的姿态去应对。此外,以我对李修的了解,安的托付,会给他带来难以名状的波动;这种波动,会给这位六十五岁的男人带来一种神勇;这种神勇会让李修总是有办法化解难题。李修后来讲了一些细节,也曲折证明了这点。
老人是在养老院去世的。疫情中,养老院很谨慎,关紧了几道门,决不允许外入。遗体的交接,安排在养老院门口的接待处。是日,李修早早在那里等候着,总算等来转运遗体的车辆。两名护工将遗体抬下车,第一项,要求李修按例填写与逝者的关系。李修在多个称谓的选择中有些犯难,他选择了“晚辈”,护工觉得不够规范,他又选择了“亲戚”。两名护工面面相觑,最后给予了通融。第二项,要求李修对遗体进行核查,并确认没有任何随身的贵重物品。两位护工退远了几步,示意李修上前。
这应该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,李修顿然觉得有双眼睛盯着自己的脊梁,让他在处理老人后事的每个环节上,不容轻慢。这双眼睛并不是别人的,是李修自己的一双道义之眼。李修事后说,他无法容忍在故人的重托之下,自己有任何马虎。他是他自己的督办者。李修在这里使用了故人二字,流露了他早年从事律师一职所留下的缜密。
李修靠近了逝者,缓缓解开白布,看见了老人的遗容,他肃穆地向老人久久鞠躬。
无人能察觉李修过速的心跳,以及经强行暗示后又归位的镇静。他细细检查了几处常佩有首饰的部位。一切复位,填完表单,车开走了。此时,李修本该如释重负,但并不是这样。
李修百感交集,这位离世的老人,三十年前曾经和李修有过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。当时气氛凝重,安不在场,尽管两个男人互相敬烟,言语体面,但本次谈话的结论,是老人拒绝李修成为自己的女婿。重陷旧日场景,几十年后,自己又成为老人唯一的送行者,李修的脸上有一丝无奈,有一丝复杂。他走向停车场,脚下的薄冰,连续发出碎裂的声响。他不是第一次感受命运的奇幻,对如此的人生布局,没有过多的喟叹。
面前是初冬街景,他抬头看见,在树杈的疏疏漏漏后面,冬日一亮一亮。有些块状积雪松动了,自高处跌下,从屋檐或树冠,李修像是没有关切。想到刚才自己对老人那个诚意的鞠躬,他心里出现了熨帖的感觉。李修为自己认真完成了一件良善的事,有些释然。
在写这篇涉及朋友离世家人的短文前,我还是问了一下安。她的回复是:我可以的,谢谢。(邬峭峰)
关键词: